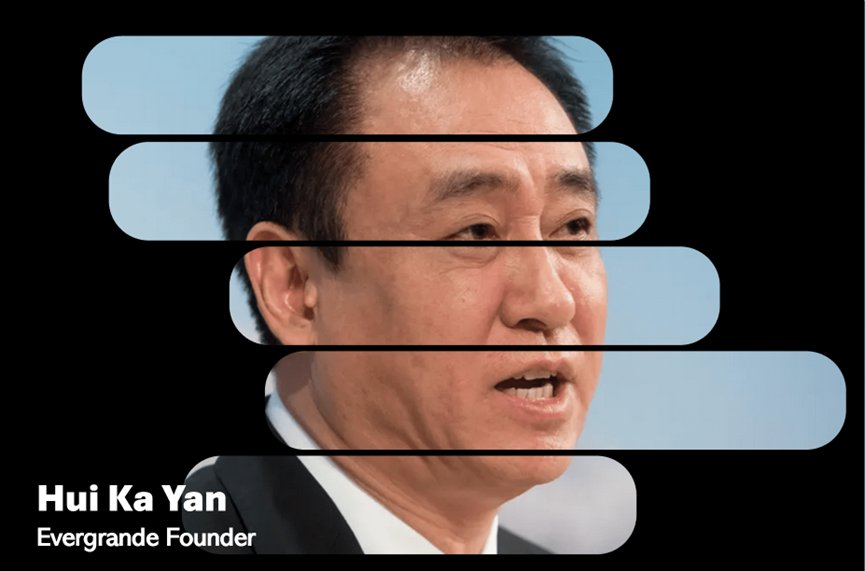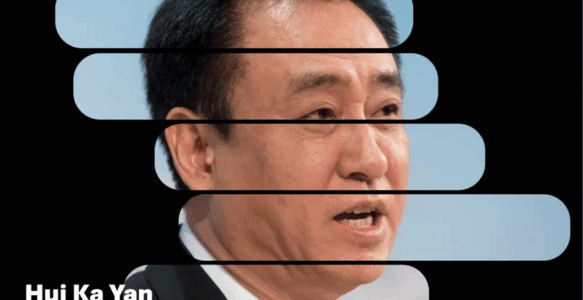中国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已从地产崩盘演变为全球跨境执法的“活教材”。
2024年1月,香港高等法院下令恒大清盘,创始人许家印(Hui Ka Yan)随即被卷入诉讼漩涡。
2025年9月16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在[2025] HKCFI 4327一案中作出裁决,任命恒大清盘人为许家印全球资产的联合接管人,覆盖价值高达77亿美元(约550亿元人民币)的财产,包括其离岸家族信托。
这一判决,不仅冻结了许家印的“影子帝国”,更以严谨逻辑串联起三个核心重点:从“是否接管”(原则门槛)→“接管什么”(范围穿透,包括信托)→“谁来接管”(身份平衡)。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层层递进,确保马雷瓦禁令(Mareva Injunction)从“纸面”转为“实效”。
扩展而言,判决书的“隐形重点”是债务人资产披露失责的后果(贯穿全文),这对中国债务人是警钟。在跨境纠纷中,“沉默”往往等于自掘坟墓。
对于希望开展境外追索的中国债权人来说,尤其是手持恒大债权的投资者,这一裁决犹如曙光,值得细细剖析。
如下简单评论后,附上该判决的中文翻译本全文。
本文来自「全球追索一百案」,一起拆解全球追索100个真实案例,由杜国栋律师团队发起并创作,聚焦于海外资产调查和境外诉讼与执行的典型案例。籍此诚邀律师同行共建「台前幕后计划」:您在前台,维护客户信任,我们隐身幕后,攻坚跨境执行,为中国律师赋能,为债权人全球追索助力。
一、案件背景:从披露失责到强行接管
恒大危机源于2021年的境外债券违约,总负债超3000亿美元。 2024年3月,恒大提起HCA 551/2024诉讼,指控许家印通过离岸结构转移资产。 6月,科尔曼法官发出全球禁令,禁止许家印处分资产,并要求7日内披露所有单项价值50,000港元以上的财产。
然而,许家印自2023年9月大陆拘留后,完全未回应,形成“总失责”(total failure)。
2025年4月,清盘人提出接管传票(Receivership Summons),9月2日聆讯后,法官于2025年9月16日裁决,合并HCMP 1080/2024。
该判决强调,许家印的“零披露”将会造成禁令实质上失效,法院须升级干预。 这不是简单冻结,不允许债务人处置资产,而是对负有高额债务的债务人资产进行接管,接管人可以积极主动管理资产。冻结是一种消极措施,而接管则是一种积极促使。
二、判决三重逻辑:层层递进的执法链条
这份判决书的精髓在于其逻辑链条:三个重点完美串联,确保禁令“落地”。欧阳何法官以披露失责为“隐形主线”,逐层论证,彰显香港司法的严谨。
1. 第一重:是否委任接管人——原则门槛的American Cyanamid原则
这是C部分的绝对核心,占判决近半篇幅。法院援引《高等法院条例》第21L(1)条,视接管人为“最后手段”,仅在“公正或便利”时行使。
法官适用采用American Cyanamid一案确定的原则,逐一审查后认为符合该原则:
(1)严重待决问题及资产损耗风险:许家印涉嫌欺诈转移,因此存在资产被耗散的“真实风险”。
(2)当前保护效力:法院前期对许家印作出的披露令失效,无法监督其资产。
(3)便利平衡:接管资产可能会损害许家印的合法权利,但这一损害可由恒大公司提供的“交叉承诺”予以补偿。
2. 第二重:接管什么——范围穿透的“信托利剑”
D部分聚焦边界,强调对许家印“影子资产”的覆盖。接管令涵盖全部资产,包括附表1的15家BVI公司(100%实益拥有于许家印),本质上直击其家族信托。
法官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查布拉”管辖权,从而刺穿公司面纱,并将许家印的信托视为仍由其“实质控制”工具。
据此,接管人有权调查、恢复注销公司、扣押文件,防止二次耗散。
这一重递进至“实效”:不止冻结个人不动产、银行账户(已冻7个账户),还“穿透”离岸网络,锁定潜在数十亿美元信托资金。 对债权人而言,这是“解锁债务人资产大门”的关键。
3. 第三重:谁来接管——身份平衡的“常识机制”
E部分化解争议:恒大的清盘人获委任成为许家印资产的接管人。而许家印反对,因为接管人的身份不独立,这意味着原告接管了被告的资产。但是,这其中存在利益冲突,因为原告作为接管人有损害被告利益的利益倾向。
法院认为虽然“独立原则”为接管人的一般规则,但强调酌情灵活,采用“常识方法”:清盘人熟悉恒大事务近两年,由其作为接管人,可避重复成本。
为防利益冲突,法院引入“监督律师”。监督律师有权“识别、保障及保全”许家印的利益,但不干涉双方辩护。而监督费用暂由恒大资产支付。这重平衡,既确保执行高效,又不失中立。
后续,我们将撰写其他文章,进一步深入介绍。
三、法律原则:披露失责的“隐形警钟”
这份判决的隐线是许家印未尽到披露财产的义务,这是引发这一系列措施的核心。为此,法官援引Akai、Derby等判例,强化“美国氰胺”在香港的适用。
对大陆债务人,这也是一个警钟:
跨境禁令下,如果债务人怠于遵守资产冻结禁令和资产披露命令,则将触发升级的措施,即资产遭到全盘接管。接管人可以积极主动处置资产,这比仅仅消极冻结资产而言,对债务人影响更大。
对恒大债权人,此裁决是转机:清盘人可追回23亿美元信托,其他债权人当然也可以。其他债权人需要抓紧利用清盘人创造的时间窗口。
如下为本案件判决中文全文
HCA 551/2024 及 HCMP 1080/2024
[2025] HKCFI 4327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
原讼法庭
诉讼案号2024年第551号 及
杂项诉讼案号2024年第1080号
原告
中国恒大集团(中國恒大集團)(清盘中)
与
被告
许家印(HUI KA YAN) 第一被告
夏海钧(XIA HAIJUN) 第二被告
潘大荣(PAN DARONG) 第三被告
信信(英属维尔京群岛)有限公司(XIN XIN (BVI) LIMITED) 第四被告
丁玉梅(DING YUMEI) 第五被告
耀华有限公司(YAOHUA LIMITED) 第六被告
怡荣控股有限公司(EVEN HONOUR HOLDINGS LIMITED) 第七被告
何昆(HE KUN) 第八被告
(由科尔曼法官阁下于2025年2月12日的命令合并审理)
发官:Hon H. Au-Yeung J 在秘密审理(公开审理)
聆讯日期:2025年9月2日
裁决日期:2025年9月16日
裁决
A. 引言
1. 本案背景已在多项裁决中阐述,包括China Evergrande Group v Hui Ka Yan & Others [2025] HKCFI 689 及Re China Evergrande Group [2024] 1 HKLRD 1128,[2024] HKCFI 363。
2. 简而言之,中国恒大集团(“恒大”)于2024年1月29日被Linda Chan法官命令清盘,并由Edward Simon Middleton先生及黄咏诗小姐获委任为联合及各自清盘人(“清盘人”)。2024年3月22日,恒大针对第一被告(“许”)及其他人士提起HCA 551/2024一案。2024年6月24日,科尔曼法官针对许作出马雷瓦(Mareva )禁令,该禁令禁止其处分(其中包括)其全球资产,直至价值77亿美元(“禁令”)。许亦被命令向恒大披露(其中包括)以下资料,并须于7日内提交誓章确认:
“所有[其资产]个别价值为50,000港元或以上的资产,无论位于香港境内或境外,无论以[其]本人名义持有与否,以及无论单独或共同拥有,提供所有此类资产的价值、地点及详情”
(“披露令”)
3. 各方并无争议,许完全未有遵守披露令。
4. 因此,恒大于2025年4月3日提出传票(“接管传票”),并申请(其中包括)命令委任恒大清盘人为许全部资产及事业的联合及各自接管人及经理人,条款如接管传票附上的草拟命令所列。
B. 法律原则
5. 《高等法院条例》(香港法例第4章)(“条例”)第21L(1)条规定:
“原讼法庭可通过命令(无论临时或终局)授予禁令或委任接管人,在原讼法庭认为公正或便利的所有案件中。”
6. 资深大律师Abraham Chan提出,就“公正或便利”而言,本庭应遵循Stone法官在Stone J in Akai Holdings Limited & Others v Ho Wing On, Christopher & Others(HCCL 37/2005 及 HCCL 40/2005,未刊登,2009年9月1日)一案中所采用的方法,如下:
“41. 我接受这一命题,即有长期且确立的权威表明,若马雷瓦命令被违反,或存在真正违反风险,则适当补救是委任接管人接管受马雷瓦命令约束的资产:见《德比诉韦尔登(第3及4号)》[1990] Ch 65 及《德比诉韦尔登(第6号)》[1990] 1 WLR 1139。
42. 正如Gee on Commercial Injunctions (5 th ed)在第16.08段所述:
‘若(1)资产面临被耗散或以其他方式处于危险中,且(2)无法通过禁令满意地保存,则委任接管人可能合适。此情况发生在被告控制海外信托或公司网络,且其事务安排如此复杂,以至于若不采取该步骤,他可能成为无资判决人。委任接管人将是有效救济,而单独禁令则不然……其他需要委任接管人的情况示例包括被告可能无视禁令行事或已如此行事……’”
7. 在我看来,Akai一案判决中的以下部分亦相关:
“44. 亦宜记录,赖特先生强烈主张,马雷瓦救济授予原则与此类案件中委任接管人申请原则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不应采用American Cyanamid Co v Ethicon Ltd规则’,且须高度重视‘公正及便利’的伞状原则,尤其在本庭尚未有机会最终裁定事实事项的情况下。
45. 恕我直言,我不同意,至少不同意完全摒弃American Cyanamid规则。在此方面,我敬同意Kwan法官在Re Chime Corporation( HCMP 4146 of 2001 HCMP 4146/2001,判决日期2003年6月25日)中所表达的观点,该法官考虑临时申请委任接管人的权力;她观察如下:
‘39. 临时申请委任接管人的权力是一种酌情权力,应灵活行使,其基础类似于临时禁令,且 American Cyanamid Co v Ethicon Ltd [1975] AC 396的原则适用(Chinese United Establishments Ltd v Cheung Siu Ki [1997] 2 HKC 212 at 223; Re Niceline Co. Ltd , HCCW No. 423 of 2002, 22 January 2003, paras 50 to 53; Re Full Bullion Shipping Ltd , HCMP No. 2423 of 2002, 28 March 2003, paras 17 and 18)。
40. 我在此采用的方法……是评估并平衡以下事项:
(a) 是否存在严重待决问题;
(b) 遗产资产耗散的指称风险;
(c) 当前保护制度及其效力;及
(d) 若委任则对Chime Group及Mrs Wang利益造成的损害风险,以及是否可通过损害赔偿交叉承诺充分补偿。’”
8. 资深大律师Abraham Chan亦援引China Metal Recycling (Holdings) Limited (in compulsory liquidation) & Another v Chun Chi Wai & Others (HCA 1412/2013, unreported, 5 February 2016)一案。在该案中,原告处于强制清盘中,其针对被告的诉讼由原告清盘人继续处理,他们指称(其中包括)第一及第十三被告与其他被告欺诈共谋,通过一系列虚构交易及虚构资金流胀大原告业务的價值,从而导致原告遭受超过50亿港元的损失及损害。法院面前的问题是原告申请委任临时接管人接管特定公司及其三家子公司和母公司的资产,基于该公司已被用于耗散上述第一及第十三被告的资产。在其裁决中,基思副高等法院法官有以下表述:
“16. […] 该权力可在公正或便利时行使(见《高等法院条例》(第4章)第21L(1)条),且法院通常会认为若有充分证据证明违反马雷瓦禁令,则公正或便利(……)
17. 法院适用的证据审查,在我看来正确,是American Cyanamid规则审查。该审查由Kwan法官在Tan Man Kou v Chime Corporation Ltd and others (HCMP 4146/2001,未刊登,2003年6月25日)中确认,并由Stone法官在 Akai Holdings Limited (in compulsory liquidation) and others v Ho Wing On Christopher and others (HCCL 37/2005)(HCCL 37/2005,未刊登,2009年9月1日)中遵循。因此,法院将确定是否存在严重待决问题及资产耗散风险,将考虑当前保护寻求委任接管人一方利益的制度的效力,将评估若委任接管人则对任何一方造成的损害风险及该损害是否可通过损害赔偿交叉承诺充分补偿,以及在特定情况下是否适合较不严厉的补救。就最后一点,Stone法官在Akai一案中认为,若被告故意扣留披露,从而剥夺原告根据马雷瓦禁令有权获得其资产资料(以监督其遵守),则法院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建议,即较轻补救或部分接管足以,因为(i)鉴于缺乏披露,法院及原告根本无法评估较轻补救是否足以保护原告利益,且(ii)被告完全有权通过充分披露或提供担保结束接管。”
(强调添加)
9. 然而,尽管有上述权威,资深大律师Barrie Barlow(连同Vincent Chen先生)提出,American Cyanamid规则审查并非应采用的正确审查。主张认为,临时接管人委任申请人须令法院信服此类委任是必要的,且存在资产损失或耗散的迫在眉睫危险。
10. 为支持其陈述,他们首先援引新加坡上诉法院《Wallace Kevin James v.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Bank Ltd [1998] 1 SLR 785一案,其中在[18]段裁定:
“[…] 委任接管人的额外补救仅在尽管已有全球马雷瓦禁令提供相当保护,但仍存在上诉人及/或其妻资产损失或耗散的迫在眉睫危险,且若不委任接管人则如此,方可合理化。整个目的是防止上诉人耗散任何资产,并保存其直至诉讼结果。判决前授予全球马雷瓦禁令本身是一种严厉措施,仅在极特殊情况下命令:Republic of Haiti & Ors v Duvalier & Ors [1990] 1 QB 202 at p 215; SSAB Oxelosund AB v Xendral Trading Pte Ltd [1992] 1 SLR 600 at p 607;且委任接管人的命令更为例外。”
(律师强调)
11. 新加坡上诉法院援引维多利亚州最高法院合议庭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td & Others v Bond Brewing Holdings Ltd & Others [1991] 1 VR 386一案,其中在541页裁定:
“委任接管人的权力性质严厉,在65 American Jurisprudence (2d) para 20提及的裁决中强调,其中引用权威支持以下命题,即该权力是一种严厉、严苛且危险的权力,应谨慎行使,接管是一种严厉措施,仅在紧迫情况下允许,且仅以勉强及谨慎授予,且委任接管人是一种非凡且严厉的补救,仅在法院信服若不行使则存在迫在眉睫损失危险时,以最大谨慎行使。”
(律师强调)
12. 由于新加坡上诉法院认为该案事实中并无任何资产损失或耗散的迫在眉睫危险,最终裁定下级法院不应委任接管人。
13. 不可争议的是,委任接管人是严厉的,且法院行使该权力应谨慎。然而,我不认为此类权力仅在证明“资产损失或耗散的迫在眉睫危险”时方可行使。在我看来,新加坡上诉法院提及此类“迫在眉睫危险”,是因为其在该案事实中考虑委任接管人的酌情行使是否合理。归根结底,法院应考虑是否需采取进一步步骤以保存受访人的资产。这就是新加坡法院考虑“全球马雷瓦禁令已提供的相当保护”是否充分的原因(见上文[10]引述的判决[18]段)。
14. 亦应注意,新加坡上诉法院亦引用Derby & Co Ltd & Others v Weldon & Others (15 November 1988) (在其判决中描述为“著名”)一案,其中尼古拉斯·布朗-威金森副首席法官在第27页称:
“第一个法律问题,并未令我费心……是马雷瓦禁令下是否可委任接管人。在我看来,显然可以。若马雷瓦命令下冻结资产的适当保存需引入接管人持有某些资产,我看不出法律上为何不应委任此类接管人。”
(强调添加)
15. 因此,可见问题是适当保存资产是否可在不委任接管人的情况下实现。
16. 许方律师随后援引Macau First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v Ding Xiaohong & Others(CACV 193/2011,未刊登,2012年7月31日)一案,该案系上诉当时副法官委任接管人的命令([2011] 3 HKLRD 27)。
17. 在原讼法庭裁决中,该副法官裁定:
“10. 实质上,[委任接管人及经理人保存资产直至争议最终裁定的申请]基于[申请人]的主张,即其而非DG提供资金,并一直是土地、花旗恒大大厦及公司的唯一实益拥有人。该申请旨在防范DG尽管有DG承诺,仍存在明确资产耗散风险。
[…]
35. [委任接管人及经理人保存资产直至争议最终裁定的申请人]依赖以下资产耗散风险或上海巴鼎公司/公司或上海巴鼎管理不善的理由支持其申请:
[…]
38. 法院根据《高等法院条例》第4章第21L(1)条有权委任接管人‘在原讼法庭认为公正或便利的所有案件中’。
39. 临时申请委任接管人的权力是一种酌情权力,应灵活行使,其原则类似于授予临时禁令,且American Cyanamid原则适用。Chinese United Establishments Ltd v. Cheung Siu Ki & Anr [1997] 2 HKC 212; Re Niceline Co. Ltd . [2003] 2 HKLRD 725。换言之,法院需考虑以下问题:
(i) 是否存在严重待决问题;
(ii) 是否存在真实资产耗散风险;
(iii) 是否无或无当前有效保护制度,且应提供某种临时保护以保存现状;
(iv) 若委任则对公司造成的损害风险,以及是否可通过损害赔偿交叉承诺充分补偿。”
(强调添加)
18. 许方律师主要依赖于终审法院Yuen上诉法官在上诉中推翻副法官委任命令的判决中所陈述:
“42. 确立法律是,委任接管人是最后手段。正如法官正确所述(资深大律师Abraham Chan并未挑战),委任接管人仅在‘尽管DG承诺已提供相当保护,但若不委任接管人则仍存在资产损失或耗散的迫在眉睫危险’时方可合理(第46段)。”
(Yuen上诉法官强调)
19. 主张认为,上诉法院上述判决显示“资产损失或耗散的迫在眉睫危险”是委任接管人的先决条件,必须存在。
20. 恕我直言,我不同意。
21. 在我看来,Yuen上诉法官所言不应孤立及脱离语境解读。须铭记,正如原讼法庭裁决[10]及[35]段(上文[17]引述并突出)所指,“资产耗散风险”被依赖作为支持委任接管人申请的理由。这就是Yuen上诉法官聚焦该特定方面的原因。
22. Macau First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Limited上诉法院判决亦显示,被告的主张即American Cyanamid原则不适用并无道理,因为其并未质疑副法官在上文[17]引述的审查表述。第一审裁决仅被推翻,因为上诉法院认为原审法官在考虑是否有效保护到位时,未能考虑相关事项。
23. 最后,许依赖于Wong Luen Hang & Another v Chan Yuk Lung & Others(HCMP 2906/2016,未刊登,2017年1月12日),其中Kwan上诉法官有以下表述:
“19. 原告主张,法官原则上错误地认为临时接管人仅在法院信服其必要性时方可委任,否则不行(第5项理由)。他们主张这太过严格,审查并非必要性,而是根据《高等法院条例》第4章第21L(1)条的措辞,即‘公正或便利’。
20. 我们不接受此陈述。第21L(1)条系关于授予禁令及委任接管人的一般规定,无论临时或终局。为获得该规定适用于特定情况的进一步指引,有必要参考已决案件。我们在此关注的是委任临时接管人,非特定资产,而是3家公司全部资产及事业,且至少一家是贸易公司。权威观点认为,对于此类极端严厉补救的授予,法院管辖权须极大谨慎行使,且仅在信服该命令必要性而非其他较不侵入性及更可逆转救济时方可。Bond Brewing Holdings Ltd v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Ltd (1990) 1 ACSR 445 ,第456至458页常被本港法院在此方面引用。另见Macau First Universal International Ltd v Ding Xiaohong & Ors , CACV 193/2011, 31 July 2012, §42; Wong Luen Hang & Anr v Chan Yuk Lung & Ors , HCMP 2481/2015, 5 November 2015, §13.”
(律师强调)
24. 恕我直言,我看不出Wong Luen Hang一案可以如何支持许的主张,即恒大向法院提出的审查错误。相反,我认为该案权威进一步支持恒大关于适用法律原则的陈述,因为可见关上诉法官已明确(无任何不利评论)提及副高等法院法官李碧君采用American Cyanamid审查[1]。
25. 在考虑各方引述的权威后,我接受资深大律师Abraham Chan的陈述,即其事实上在采用委任接管人的适用法律原则方面一致。
26. 我总结适用法律原则如下:
(1) 根据条例第21L(1)条,原讼法庭可若公正或便利则委任接管人;
(2) 临时申请委任接管人的权力是一种酌情权力,应灵活行使,其原则类似于授予临时禁令,且American Cyanamid原则适用;
(3) 因此,法院将考虑以下问题:
(1) 是否存在严重待决问题;
(2) 是否存在真实资产耗散风险;
(3) 是否无或无当前有效保护制度,且应提供某种临时保护以保存现状;及
(4) 若委任则对受访人造成的损害风险,以及是否可通过损害赔偿交叉承诺充分补偿。
27. 许方律师主张,委任其资产接管人及经理人是严厉措施,因此法院应谨慎行使此酌情权,且仅在必要时委任。我同意。话虽如此,我认为所谓“必要性”要求已被American Cyanamid原则下的第3个问题涵盖(见上文[26(3)])。问题是当前保护制度是否足以保存现状,这是马雷瓦禁令的原始目的。
C. 是否应委任接管人
C1. 严重待决问题及真实耗散风险
28. 在授予禁令并随后延续针对许的禁令时,法院已信服存在严重待决问题,且许存在真实耗散风险。许并未上诉禁令。因此,我无需就此两个标准进一步陈述。
C2. 当前保护制度的效力
29. 显而易见的是,可作为马雷瓦禁令的附带命令作出披露令,以使禁令有效。
30. 然而,在本案中,毋庸争议的是,许完全未能遵守披露令。因此,存在违反法院命令。
31. 因此,恒大代表主张(我接受),无法监督禁令,且委任接管人是恒大获得本应由许披露的资料的唯一方式。
32. 许提出多项论点反驳上述论据。
33. 首先,称虽然许承认未能遵守披露令,但各方共识是因其被拘留于内地。因此,其不遵守并非“故意”且因此不可归责。
34. 此类陈述的基础是许方律师Justin Chow先生的确认,该确认基于其据称从许的内地律师(甚至未命名)处获悉的资料(其中包括),自许被拘留以来,其无法处理任何其资产或其控制下的资产,且被内地当局禁止与任何人讨论相同事宜。恐怕我无法接受此类证据,原因如下:
(1) 虽然Chow先生的证据是传闻证据,但他未命名信息来源,除称其“从许的内地律师”处获悉,且不清楚该内地律师如何获得据称信息;
(2) 假设Chow先生已获许适当授权辩护此申请并作出其确认(我无理由假设不然),难以理解(且Chow先生未能解释)为何许会被禁止讨论其资产。
35. 无论如何,我不认为许的责任相关。毕竟,问题是鉴于许完全未提供任何披露,在当前情况下是否必要作出委任,以使禁令有效维持现状。
36. 其次,许方律师主张,委任接管人并非必要,因为尽管未披露,清盘人已能识别许相当数量的资产。
37. 恐怕此论点注定被驳回。虽然确实识别多项资产,但恒大根本不知许的总资产为何(就其价值不超过禁令上限而言)。
38. 第三,就不动产和银行账户而言,许方律师提交称,一旦物业登记机关和银行已收到禁令令状(Injunction Order),这些资产被转移或处分的可能性实际上已不存在,因此没有必要再指定接管人。
39. 在此方面,我同意恒大资深大律师Abraham Chan的观点:
(1) 仅仅向物业登记机关送达文件并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因为本案并不涉及任何与土地或土地权益有关的请求;
(2) 许的论点预设其所有银行账户均以其本人名义持有。然而,根据米德尔顿先生的证据,清算人的调查显示,许及其关联人存在利用代名公司持有资产的明显模式。事实上,可以看到,大量并非以许名义登记的银行账户同样已被禁令令状冻结。
40. 第四,就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公司而言,虽然这些公司已被注销(struck off),但有意见认为,即使没有接管令,也可以恢复其登记。
41. 然而,为了保全许的资产,仅仅将这些BVI公司恢复至公司注册名册上并不足够。尤其是在明显可以看出许本人无法维持这些公司的情况下,更应采取措施,防止这些公司再次被注销。
42. 此外,此类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均为“附表1公司”(见下文[55]–[56])。调查此类公司事务合理且必要。
43. 在考虑各方论点后,我信服,在许完全未能披露其资产的情况下,作为最后手段委任接管人是必要的,否则禁令无法充分有效保存现状。
44. 事实上,在我看来,许一方所提出的主张与披露令(Disclosure Order)的条款相悖,因为他们现在声称,尽管完全未遵守该命令,法院也无需对此采取任何措施。若接受这一主张,就等于承认当初根本无须作出披露令。这显然是不对的。
C3. 便利平衡
45. 此处问题是若委任则对许造成的损害风险,以及是否可通过损害赔偿交叉承诺充分补偿。
46. 在我看来,即使许因拟议委任接管人而遭受任何损害,其可由恒大的损害赔偿交叉承诺充分补偿。
47. 许方律师Justin Chow先生确认,鉴于拟赋予清盘人的权力,许辩护本案的能力将严重受损。
48. 进一步指称:
“[…] 就我所代表的律师事务所而言,鉴于清算人在接管令草案第[4.11]条项下所享有的权力,如果清算人依据该条行使权力并向本所发出‘指示’,则本所与许先生及其中国律师之间将会产生有关律师职业保密特权的复杂问题,同时还会涉及遵守相关中国法律的困难。”[2]
49. 虽然许方律师确实主张,“在像本案这样具有对抗性的民事诉讼中,法院实际上不可能任命许的诉讼对手为其(剩余)资产的接管人”,但律师并未进一步依赖Chow先生所声称的“偏见”理由。
50. 无论如何,为求完整起见,我必须强调,我不同意许的抗辩会因拟议中的接管令而受到任何不利影响。即便接管人被任命,他们的权力仅限于识别、保障并保全许的资产,而无权干预许在本案中的抗辩。在我看来,Chow先生对接管令草案第4.11条的担忧,源于他对该款的误解。该款应与草案第2条及第4条主体部分一并解读,而这些条文已明确表明,接管人的任命目的在于在本案判决前保全和保障资产,并确保遵守禁令令状(Injunction Order)。
51. 许方律师还主张,拟议的接管人任命本质上具有“侵入性”。甚至有人提出,如果作出接管令,将构成对《基本法》第105条的违反。该条款(除其他外)“保障个人及法人的财产取得、使用、处分和继承的权利”。
52. 法院一向承认接管令具有侵入性。这正是为何早有定论——此类命令应仅作为最后手段作出,且法院应先考虑是否存在较温和的救济方式。然而,本案的问题在于,许完全未作任何披露,因此恒大根本无法有效监督马雷瓦禁令的执行。
53. 至于许所援引的《基本法》权利,该论点的简要答复是:他的权利并非绝对。事实上,他对自身财产的处置权已因禁令而被限制,而他并未就该禁令提起上诉。
54. 总而言之,我认为原则上应当任命接管人。至于接管令的范围及接管人的具体人选等剩余问题,我将在下文进一步处理。
D. 命令范围
55:关于接管令的适用范围,概括而言,许的论点如下:
(1) 禁令仅针对许本人、第二被告、第五被告及第八被告作出;
(2) 法院仅对第五被告(许的前妻)行使了 Chabra 管辖权;
(3) 法院并未对第四被告或《接管申请传票》(Receivership Summons)附表一中所列的其他14家公司(统称“附表一公司”)作出马雷瓦禁令(Mareva injunction);
(4) 因此,法院不应就第四被告自身的资产任命接管人,也不应授予他们管理第四被告事务的权力;
(5) 法院还应避免任命接管人行使超出禁令令状范围的权利或权力,例如:
(1) 调查附表一公司的事务;
(2) 将附表一公司全部或部分资产登记在接管人或其代名人名下;
(3) 查封附表一公司的账簿、记录及文件;
(4) 就上述事项采取其认为“必要或适当”的任何行动。
56.许的上述主张被驳回。与其律师的陈述相反,附表一公司(包括第四被告)均在禁令令状附录C中被定义为“与许有关联的公司”。更为重要的是,禁令令状第1段规定如下:
“第一被告不得,无论以其本人名义或通过其雇员、代理人:
(1) […]
(2) 以任何方式处置、处理或减少其任何资产的价值,无论这些资产位于香港境内或境外,无论是否以其本人名义持有,亦无论为单独或共同所有,直至总额达港币六百亿元(HKD 60,000,000,000)。该禁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资产:
(a) […]
(b) […]
(c) 本令附录C所列公司的财产与资产,或其出售所得款项(如相关资产已被出售);
(d) 本令附录D所列银行账户中的任何资金。”
57. 此外,就披露令而言,许及第二被告已根据禁令令状第7段被命令:
“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原告其所有单项价值达港币五万元或以上的资产,无论这些资产位于香港境内或境外,无论是否以其本人名义持有,亦无论为单独或共同所有,并说明这些资产的价值、所在地及详情,包括但不限于:
(a) […]
(b) 本令附录C所列公司的资产,或若相关资产已出售,则应说明其出售所得款项的现存去向。
[…]”
(强调添加)
58. 因此可见,禁令明确涵盖了附表一公司(包括第四被告)。根据该禁令,集团有权了解这些公司的资产状况。在这些公司资产完全未被披露的情况下,必须赋予接管人查阅这些公司文件的权力,以确保禁令得到遵守。简言之,所请求的权力并未超出禁令令状的范围,而许关于“当事人自主”的论点,在本案情形下是错误的。
第59段:我亦注意到副法官Edward Bartley Jones QC在 Dadourian Group & Others v Azuri Ltd [2005] EWHC 1768 一案中的观点,该观点已被上诉法院在 Akai案(HCMP 1718, 1720 & 1722/2009,未公开判决,2009年9月24日) 的判决理由中引用(该案驳回了针对Stone法官作出的接管令的上诉许可申请):
“26 对第三方作出冻结禁令的法院管辖权是毫无疑问的。该管辖权的行使,本质上是作为对被告冻结令的辅助救济。若有充分理由认为第三方的资产实质上是受禁令限制的被告的资产(参见 SCF Finance Co Ltd v Masri [1985] 1 WLR 876,Lloyd上诉法官第884B-F页),法院可行使该管辖权。典型情形是,当有充分理由认为第三方代表被告以代持信托(bare trust)或代名形式持有资产时。然而,我拒绝认为‘Chabra管辖权’仅限于此类情形。正如Robert Walker法官在 International Credit and Investment Co (Overseas) Ltd v Adham [1998] BCC 134 案第136页指出,随着英国高等法院愈发频繁地处理国际重大欺诈案件,法院在适当情形下会采取果断措施,不允许其命令被通过秘密离岸信托和公司结构所规避。这种情形无疑构成所谓‘影子信托与公司’的案例。Robert Walker法官进一步指出,当被告能够轻易在这些影子实体之间转移真实资产,致使追踪困难时,冻结令是合理且必要的。这正是法院透过离岸公司架构以识别真实资产、乃至‘揭开公司面纱’的正当理由(尽管该比喻生动但并不精确)。Cumming-Bruce上诉法官亦在 Re a Company [1985] BCLC 333 一案第337-338页指出,法院若为实现公义,即使无论公司结构的法律效力如何,亦可行使权力揭开公司面纱。”
“30 就我而言,我认为无需在严格信托法意义上证明受益所有权。显然,若资产以‘代持信托’形式持有,则可行使Chabra管辖权。但即便被告对相关资产并无严格法律或衡平法上的权利,只要其对该资产具有某种权利、控制权或接触权,该管辖权仍可行使。关键在于‘实质控制’。正如 Gee on Commercial Injunctions(2004年第五版,第13.007段)所述,若被告设立信托和公司网络以控制资产,从而规避判决执行,则对相关非当事人授予冻结救济是适当的。我同意这一观点。应当关注的是控制的实质现实,而非形式上的信托法分析。即便资产被置于自由裁量信托中,若事实表明被告实际控制该信托的运作,法院仍可行使Chabra管辖权。任何其他解释都将削弱法院的执行力,使其命令被虚构结构规避,与Robert Walker法官在前述案件中的原则背道而驰。”
60. 在本案中,应注意到,附表一公司均由许百分之百实益拥有。因此,这些公司的资产被禁令令状所涵盖,完全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基于同样的理由,赋予接管人管理这些资产的权力,同样公正且便利。
61. 为求完整,我还应提及《接管申请传票》附表二中列明的银行账户。其中部分账户并非以许名义开立,而是由若干有限公司(“其他账户持有人”)持有。然而:
(1) 这些账户已被列入禁令令状附录D,因此已被相应冻结(见第56段);
(2) 这些其他账户持有人均已列入禁令令状附录C。
62. 另一项由高级大律师Barrie Barlow提出的异议涉及接管令草案第5.7条,其内容如下:
“5. 为执行上述第2段所确定的目的,并在合理必要的范围内,接管人被授权:
[…]
5.7 采取其认为为实现任何资产、或附带或有助于其依据本命令享有的任何权利、权力及自由裁量权所必要或适当的所有其他行为。”
63. 他正确地指出,该条款可能赋予接管人处置许资产的权力。
64. 对此,恒大的资深大律师Vincent Chen先生向本院表示,他同意在最终命令中删除该条款。因此,本院将不会赋予被任命的接管人此项权力。
E. 接管人身份
65. 恒大提议委任清盘人为接管人,理由如下:
(1) 许个人事务似乎与恒大事务紧密交织,且许个人财富显著部分显然源自恒大;
(2) 清盘人已积极调查恒大事务(极其复杂)近2年;
(3) 鉴于清盘人对案件的积累知识:
(a) 鉴于其熟悉相关背景,其可立即开始工作;
(b) 可避免迄今调查成本重复;
(c) 亦可避免未来工作重复。
66. 拟议接管人身份遭许强烈反对。主张委任许的敌对诉讼对手为其全部剩余资产接管人不合适。
67. 资深大律师Barrie Barlow及Vincent Chen先生援引了 Kerr & Hunter on Receivership and Administration (22 nd edition),书中博学的作者在第 2.1 段中阐述如下:
“概述 法院委任的接管人是:
(a) 公正无偏的个体,独立于争议各方;[一般原则为 “应任命完全中立的人士”:参见Fripp v. Chard Railway (1853) 11 Hare 241 at 260,大法官佩奇·伍德在第 260 页的判词;另见第四章]
(b) 由法院应一方申请委任;
(c) 在诉讼前、诉讼中或判决后;
(d) 收取、保护及接收受访人资产。”
(律师强调)
68. 虽然认可上述描述为“一般规则”,但我不认为应视其为不可灵活规则。毕竟,委任接管人涉及法院酌情行使。法院应考虑整体情况并决定何命令最适合案件。事实上,在Kerr & Hunter中,作者亦在第4-4段称,在适当案件中,若信服委任将对遗产有益,则法院可委任对申索标的感兴趣人士为接管人。
69. 在Re Orient Power Holdings Ltd [2008] 2 HKLRD 494中,Kwan法官面对委任清盘人的情况,其需解决的问题是是否应委任由有担保债权人委任的公司接管人及经理人之一的萨顿先生,连同两名不同会计师事务所拟议独立委任人作为清盘人。官方接收人反对拟议委任,因为认为利益冲突潜力太大,且将树立坏先例。她的判决[34]段有以下表述:
“在恒大破产中,利益冲突潜力可能出现在多种事项,如公司间余额、对资产的竞争申索、负债分配、保证及赔偿申索、抵销或双重证明问题、保安有效性、税务及避免或追回行动。一般而言,认可对恒大内公司委任共同清盘人符合全体债权人利益,而非每家公司单独清盘人。法院未采取严格避免冲突及不允许同一人行动的要求,而是采取常识方法,并在可能有效管理冲突的情况下作出委任,通过视每案情况而定的适当措施。此类措施示例包括获得独立法律意见、委任同一事务所额外合伙人、委任不同事务所独立合伙人。无论冲突是潜在或实际;问题是此类冲突是否可有效管理。若不可管理,则不作委任。上述是对Sisu Capital Fund Ltd. & Ors. v. Tucker & Ors . [2005] EWHC 2170 (Ch) at paras. 91 to 120讨论的总结。”
70. 虽然本案并非完全相同情况,但我看不出为何不应在此采用相同“常识”方法。在清盘人获委任为接管人的明显优势情况下,问题是此类委任是否可能引发利益冲突,且即使如此,该冲突是否可管理。
71. 在我看来,不太可能存在此类利益冲突。这是因为赋予接管人的权力仅为根据禁令识别、保障及保存资产。其将无权以任何方式干涉许在本案的辩护。例如,若许根据禁令条款请求释放资金支付其法律费用,无理由(许方律师亦未提出此类建议)接管人作为法院官员会拒绝其请求。
72. 无论如何,即使存在任何冲突,可通过恒大提议的“监督律师”委任管理。根据草拟令,接管人须定期向“监督律师”报告并回答“监督律师”合理提出的所有问题。若识别任何利益冲突或潜在冲突,接管人及“监督律师”须就解决该(潜在)冲突的步骤达成一致。若无法就该事项达成共识,接管人有权向法院寻求指示。最重要的是,提议接管人不得在(潜在)冲突解决前就该事项采取进一步步骤。
73. 因此,我结论应委任清盘人为接管人。
74. 就“监督律师”身份而言,恒大提出4名供本庭选择。似乎其对谁获委任无偏好。另一方面,许方律师未对任何候选人作出不利评论。
75. 在4名候选人中,委任其中一人绝非直截了当,因为需从该特定律师当前某些客户处获得进一步批准(可能或不可能)。鉴于法院获提供3名其他候选人,我倾向不选该特定律师。
76. 就剩余候选人而言,其均为经验丰富律师,其专业知识毋庸置疑。在考虑其背景及资历后,我认为应委任在Messrs. Wilkinson & Grist律师行任职的Keith Ho先生。
77. 许方律师进一步主张,许不应面临可能需支付全部接管费用的风险。这并非许当前应担忧的事,因为恒大提议接管人报酬应从恒大资产支付。虽然亦提议恒大可申请变更此安排,但该事项可在有此类申请时进一步辩论。
F. 命令
78. 基于上述理由,我作出草拟接管令[4](除第5.7段外)的命令。第7段中“监督律师”详情应据此填写。
G. 费用
79. 费用应随事件而定。我作出临时费用命令,许须承担恒大的接管传票费用。
80. 上述临时命令在14日内无变更申请(若有,将书面处理)的情况下变为绝对。
81. 恒大的接管传票费用应简易评税而非课税。除非在时限内作出上述费用临时命令变更申请,否则恒大须在上述14日期限届满后7日内提出并送达其费用声明。许须在其后7日内提出并送达其反对声明。接管传票费用的简易评税将在其后书面进行(无论许是否在时限内提出反对声明)。评税费用须由许在评税后14日内支付。
H. Au-Yeung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
原告律师:资深大律师Abraham Chan,由Karas So LLP律师行委派
第一被告律师:资深大律师Barrie Barlow偕同Vincent Chen,由Justin Chow & de Bedin Solicitors LLP律师行委派